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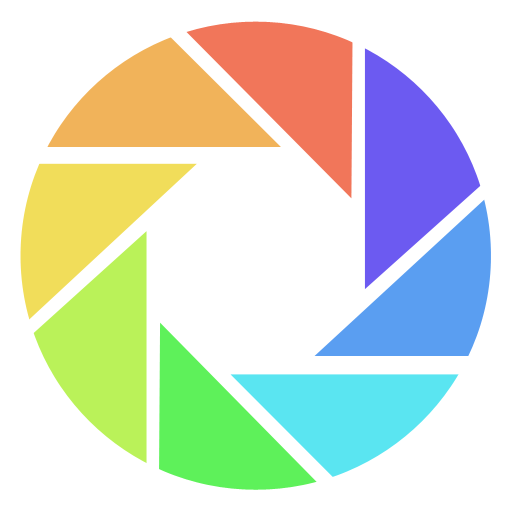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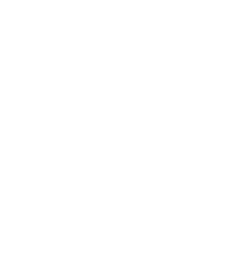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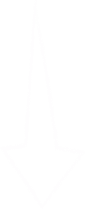
作者:高圣平、秋蓉
摘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6条规定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是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核心程序要件,但其规范效力在理论与实务中存在显著分歧。本文以该条款为中心,通过类型化分析五种学说争议,揭示其核心争议聚焦于规范性质识别、合同生效要件认定及法律后果三个层次。研究指出,从《民法典》第153条的规范构造出发,“承包方同意”规则旨在平衡承包方知情权与土地经营权人流转自由,其规范目的不否定合同效力,应界定为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同时,该规则不构成法定生效要件,违反仅导致承包方取得原流转合同解除权,而非再流转合同无效。
一、学说分歧与争议类型化:五种解释路径的规范层次
关于未经承包方同意的再流转合同效力问题,学说见解与裁判立场呈现多元化格局,主要形成五种解释路径:其一,再流转合同无效说;其二,再流转合同有效说;其三,再流转合同未生效说;其四,承包方享有流转合同解除权;其五,承包方享有再流转合同解除权。[1]此争议核心可类型化为三个规范层次:前两种学说聚焦“承包方同意”规则对合同效力评价的规范性质识别;第三种学说需论证该规则是否构成合同生效要件;后两种观点则指向违反该规则的法律后果,承包方享有何种解除权。
就前两类观点之争议,对“承包方同意”规则在再流转合同效力判定中的规范性质,应依循规范识别之基本路径展开。依据《民法典》第153条之规范构造,强制性规定可类型化为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性强制规范,唯前者始得否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2]有论者主张,“承包方同意”规则旨在调整私主体间利益分配,其规范属性应界定为与强制性规范相并列的“私权限制规则”。[3]然而,土地经营权人与再流转受让人既可约定排除该规则之适用,亦可在未获承包方同意时径行缔约,此等特征表明该规则属于复杂规范,其性质识别仍需回归《民法典》第153条之规范框架。[4]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构建起了效力性强制规范识别的多元判定准则。该准则着重指出,在识别过程中,需全面权衡诸如“规范所保护的法益类别、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以及交易安全的保障”等多种要素,并明确反对不当扩张合同无效范围。《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16条规定的“合同有效是否影响规范目的实现”以及“合同无效是否导致处理结果显失公平”,可以明显看到引入了比例原则之审查思路。由此可见,在效力性强制规范之识别过程中,需在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寻求价值平衡,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审慎得出结论,于下文详述。[5]
就第三类观点之规范分析,《民法典》第502条第1款确立了合同生效的特殊规则,即法律对合同生效条件另有规定时,合同不当然自成立时生效。该条第2款进一步将法定生效要件限定于“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情形,表明未生效合同须经相关行政审批部门批准始得生效。[6]就“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规范性质而言,其既未被法律明定为合同生效要件,亦不涉及行政机关的审批权限,而仅要求取得作为民事主体的承包方之同意。因此,从规范解释的角度,“承包方同意”规则不属于再流转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7]
就后两类观点之规范分析,其核心在于判定“承包方同意”规则是否构成《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第4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违约行为”。对此,学界对此已达成相对一致的见解,普遍认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承包方同意”规则应被视为流转合同的隐含条款。根据这一规则,若未经承包方许可擅自进行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则构成第42条第4款所规定的重大违约情形,承包方有权依法解除原流转合同。[8][9][10]然而,就再流转合同的法律效力而言,由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承包方并非该合同的缔约主体。在缺乏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承包方并不具备解除再流转合同的法定权利。
二、“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规范性质:效力性强制规范之否定
从利益衡量的规范视角来看,“承包方同意”规则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通过确立承包方的信息知情权,确保承包方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仍能有效掌控土地利用状况;[11]另一方面,构建承包方与土地经营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防止土地经营权人以转手牟利为目的滥用再流转权利。[12]如此看来,立法者设置“承包方同意”规则,实质上是通过构建信息知情权的保护机制,在承包方权益保障与土地经营权人再流转自由之间寻求价值平衡。[13]
在利益平衡的规范分析框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解释》第13条所确立的“发包方同意”规则的效力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该条将“发包方同意”规则界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规定未取得发包方同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其规范意旨不仅在于维护发包方权益,更深层次在于保障承包方不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而丧失基本生活保障。[14]相较而言,“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规范效果呈现出显著差异,违反该规则仅导致承包方对农地现状的知情权受损,并不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续。相反,因“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再流转作为土地经营权的二次流转,亦属于政策鼓励的流转范畴。若仅以未经承包方同意为由否定再流转合同的效力,不但与改革目标背道而驰,还会不合理地限制土地经营权人的再次流转自由。[15]基于上述利益衡量,把“承包方同意”规则归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缺乏合理的支撑,其规范性质应界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据此,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再流转合同无效。
结语
本文通过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6条“承包方同意”规则的系统辨析,厘清了其在农地再流转中的规范效力边界。研究表明,该规则本质上是通过程序性限制保障承包方权益,而非实质性否定合同效力。司法实践中应摒弃“无效说”的僵化立场,转而采纳“有效说+违约责任”的路径,既维护承包方知情权,又促进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
[作者简介:高圣平,男,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学科带头人(挂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秋蓉,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课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集体所有制法律实现机制研究”(22&ZD202)]
参考文献:
[1]单平基.土地经营权再流转中的“承包方书面同意”[J].东岳论丛,2022(10):176-177.
[2]王利明.论效力性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以《民法典》第153条为中心[J].法学评论,2023(2):20.
[3]张素华,王年.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4):83.
[4]王轶.民法规范论视野下的合同效力[J].法律适用,2023(12):3.
[5]黄忠.《民法典》第153条的逻辑与续造[J].中国法律评论,2025(1):115,121.
[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157.
[7]单平基.土地经营权再流转中的“承包方书面同意”[J].东岳论丛,2022(10):181.
[8]房绍坤.承包地“三权分置”中土地经营权再流转方式释论[J].求索,2024(5):18.
[9]王洪平.民法视角下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规范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34.
[10]张素华,王年.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4):85.
[11]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97.
[12]何宝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115.
[13]单平基.土地经营权再流转中的“承包方书面同意”[J].东岳论丛,2022(10):178.
[14]何宝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91.
[15]王洪平.民法视角下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规范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33.
